一个企业家的人生归宿,是“见自己”...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的摩崖石刻上,儒者捧卷、道士炼丹、僧人打坐,三教造像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秘密——中华文明用儒道释三面棱镜,折射出人类认知世界的完整光谱:通过“见众生”建立伦理坐标,借由“见天地”参悟自然法则,最终在“见自己”中完成精神觉醒。
站在文明演进的十字路口,儒家的伦理温度、道家的生态智慧、佛家的心性觉悟,恰似三棱镜分解出的文明光谱,为商业实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关照与指引。
一个企业家,可能先“见自己”(追求财富证明能力),后“见天地”(理解经济规律、政策趋势),最终“见众生”(通过公益回馈社会)。也可能从“见天地”(观察自然)到“见众生”(描绘人间百态),最终“见自己”(表达独特的精神世界)。还有可能,这三重维度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见众生”时反观自身(见自己),在“见自己”后更深刻理解他人(见众生),进而关照世界万物(见天地)。
从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新著《心生之境》中,我们不难看到,被尊为“创业教父”的他,如何经由商业与生活之“境”,理解生命的多样与悲欢,认知世界的规律与浩瀚,“见天地”、“见众生”;又如何经由自洽之“心”,实现自我接纳与内心和谐,找到自己的安放之处,“见自己”。
至暗之“境”
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十年内连续创立携程、如家、汉庭(华住)三家现今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成功实现四次上市的季琦,都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
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季琦的成长之路上,经历过三次“至暗时刻”一般的危机。
第一次是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出生于江苏南通市如东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季琦,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住的房子下雨漏水、冬天进风,他很小就到田里插秧挑粪。1985年到上海读大学,每天没钱吃饱饭,晚上还得去自修,学习很辛苦,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很难融入周围的环境,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带着这些困惑,他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书籍,思考“人为什么会活着”这样的问题。
第二次危机是在如家经历的。2004年年底,一些如家董事会成员酝酿引进职业经理人担任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主要是觉得他的背景不够职业化,没有读过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没有在大公司待过,管理经验有所欠缺,处事比较急躁。
这等于向作为如家创始人的季琦,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季琦很愤懑。但一番激烈斗争后,股权不占优势的他,最终被迫离开CEO的位置,还被逼签下“竞业协议”,“两年内不得从事经济型连锁酒店行业”。
这是季琦生命中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所有的梦想都被一个很野蛮的东西破坏了,毫无道理,而自己却没有回天之力,他一度非常绝望。
“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过去的伙伴、朋友,都在那个时刻离我而去,这让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许多原来和我最紧密的人,都离开了,对我来说就像是对人生的一个彻底否定。那时候我不知道该和谁沟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次,是莫扎特的《第三十一号交响曲》拯救了他,那种和谐与执中的平衡之美,让他觉得人世间还值得。
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得猝不及防,汉庭当时正在进行第二轮融资。有一天,季琦一个很好的朋友,请他到上海兴国宾馆吃早饭。两人刚坐下,那个朋友说:“老季,我们的基金这个时候不能再投了。”
投资协议都已经签完,开酒店用的原料都采购好了,项目签了,员工也招了,按计划,资金那几天就要到账的,投资人却忽然说不投了。
不啻于晴天霹雳。
事后反思,季琦觉得,如果自己是个纯粹的生意人,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内心疼痛,毕竟对方有不投资的权利。可他容易把情感和生意混在一起,紧要关头,当一个好朋友亲口说出“不好意思兄弟”,他的绝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那天晚上,从来不失眠的季琦失眠了。
在所有公开场合,季琦都表现得无比镇定,一如往常,私下却急如星火,找了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源。当时,外界关于汉庭资金链断裂的流言四散传播。
经过痛苦的辗转反侧,季琦决定卖掉自己名下的如家股票,当时他持有如家15%的股票,是第一大个人股东。股票价值几千万美元,那时股价已经跌了很多,选择卖掉肯定不是好时机。但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如今再回想那个心有余悸的“至暗时刻”,季琦的感悟是:“危机给了我们机会。在大家都难的时候,你比别人更坚定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就能用很小的力气,得到很大的回报。”
尼采说过,“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遭遇”。
三次至暗时刻,帮助季琦完成了三次蜕变。第一次,让他的心态变得从容和淡定。第二次,让他的心胸变得开阔,学会了宽容和忍耐。第三次,让他看清了自己这一辈的使命。
季琦在自序中解释书名的时候说,我们的人生和实践都是我们“心”的产物,那些工作和生活的经历,都是心在不同时空化出的“境”。以某种极端、剧烈的方式,让他“见天地”“见众生”,这些至暗之“境”,何尝不是照亮季琦创业之路的明灯?
此“心”安处
季琦的大学专业是工程力学,曾顺着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脉络,找自己喜欢的哲学书籍读。四十五岁以后接触王阳明,从而回归东方思想,开始阅读佛教书籍,思考智慧、灵魂等课题。
南宋思想家陆九渊是王阳明心学的源头。在《中国哲学十五讲》一书的“自作主宰:陆九渊的哲学”一讲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各种要素的权衡、综合,在各种权衡、综合中,对发心动念那一念之微的分辨是至为关键的。做一件事‘最根本目的是什么’,初心是什么,这是君子小子的分野。……人的行为,这一念之差、一念之微,是分别善恶的根本: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好人,还是想成为一个坏人;你到底是出于利之心,还是出于义之心;你到底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都在这一念之微。这是陆九渊最发人深省、最大震撼人心的地方,这一念之微的分辨,是心学得以挺立的根由所在。”
人既生活于现实世界,又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被尊为20世纪中国哲学界泰斗的冯友兰自问自答:“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增加人对客观实际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
“见天地”“见众生”终究还是为了“见自己”。我这些年在研究企业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观点:企业家选择创业,就像有人选择当老师、有人选择当律师一样,那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成长方式,只不过这种成长方式伴随着更大的风险或者更大的财富而已。
最近四五年,我见到过季琦的坚韧与信念,也见到过他的焦虑与憔悴,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冲淡与从容。
季琦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心安”——
心安才能够专注,才能处身立命,否则容易随波逐流。我过去就是太急躁了,如果我能够很早地把我的心安定好,不要因为我的同年不好就变得很焦虑,我现在能够做得更好、更成功。
心安了,你做事的节奏会不一样,你对人、对你的伙伴也会不一样。我原来脾气暴躁,公司里所有的人都被我骂哭过,后来我觉得没必要那样,觉得可以多放点儿情感在里面,多点儿包容。
心安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最终要指引你去到想去的地方。
公元1082年,春寒料峭的黄州,45岁的苏轼在历尽劫波之后,写下那句流传至今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差不多950年后,季琦在《心生之境》的最后一篇随笔中自问自答:“现在是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坏时代?我觉得所谓好坏,其实取决于我们的内心。内心觉得这是个好时代,就会发现一切都很好;内心觉得这时代太坏了,那看到的就都是荒凉的景象。”
以下内容为友情赞助提供

全网新项目分享交流群
扫码进群,获取最新项目资讯
文档于: 2025-10-09 19:49 修改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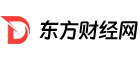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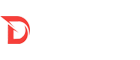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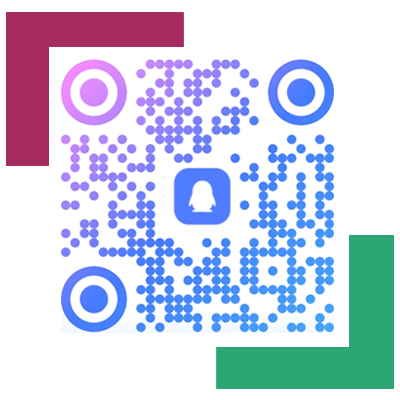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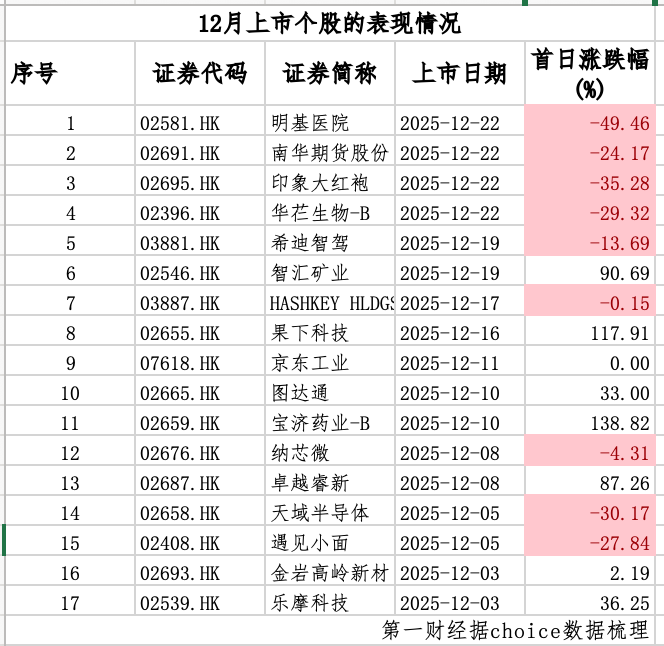
评论列表
一个企业家的人生归宿,是“见自己”...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的摩崖石刻上,儒者捧卷、道士炼丹、僧人打坐,三教造像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秘密——中华文明用儒道释三面棱镜,折射出人类认知世界的完整光谱:通过“见众生”建立伦理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