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的荷兰使团,为何被历史遗忘?...
1794年,乾隆皇帝准备举行登基六十年庆典。臣子奏请大办新春盛典:摆筵席,放烟火,办诗会,唱大戏。王公大臣将来颂贺;价值连城的礼物将进献至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和最宏伟的园林;满洲贵族、蒙古王公、回部首领、西藏喇嘛,以及朝鲜燕行使等也将远道而来。皇帝享受这普天同庆之乐。他自视为天下之君,他的朝廷便是当今世上各民族、各宗教、各色人等的中心。
听闻西洋国家荷兰希望遣使来贺,他龙心大悦。对当时的清朝人来说,欧洲人是世上最奇异的番族:卷曲的头发,形似内衣的紧身裤,还有怪异的举止。使团的正使、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和副使、精明的商人范罢览(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致信请求觐见。皇帝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自应准其来京瞻觐,遂其向慕之忱。
乾隆皇帝由此开启了前现代史上东西方关系中最有趣的插曲之一。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鲜为人知,却是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受到接待的欧洲外交使团。直到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廷被迫签署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之时,中国才再次迎接同等级别的外交使团。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荷兰使团仿佛已被人遗忘。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篇幅足以成书的研究,关于它的文章也屈指可数。教科书中见不到它,甚至一些清史研究者似乎都对它闻所未闻。我攻读中国明清史学出身,也是荷兰史专家,就荷兰在东亚的外交活动写过专门的文章,但直到我开始为写作《最后的使团》做研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当我发现这个使团在当时何等不同凡响,又是如何在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朝鲜语资料中留下宝贵的记载时,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惊讶。我开始探索这些丰富的记录,发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里充满了性格鲜明的人物、曲折惊险的航行和人与人的钩心斗角,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迷人的背景之下:在中国,起义即将爆发;在欧洲,法国军队正向阿姆斯特丹进军。我当下意识到,这段故事将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叙事史。
1795年的荷兰使团为看待18世纪的中国和中西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果决地突破“文化冲突”叙事,这种叙事至今仍渗透在我们对中国和西方的理解之中。这是因为,与当时的其他使团相比,荷兰使团是成功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施与它的恩惠和权利是其他欧洲使节都不曾享有的。正使德胜和他的上司都感到他们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与两年前访华的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遭遇相比。
马戛尔尼的失败与“文化冲突”论
荷兰使团有多么默默无闻,马戛尔尼勋爵的访华使团就有多么家喻户晓——它此行的结果却与前者大相径庭。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正是历史学家将中西方外交史视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
马戛尔尼于1793年抵达中国,携带着昂贵的礼物,率领着一众画家、科学家和音乐家,更怀揣着一系列大胆的提议。他以为这些提议有助于英国与中国建立起互利关系:两个大国强强联手。然而,皇帝和他的朝廷不信任马戛尔尼:此人不但拒行跪拜之礼,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妄有渎请)。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英国人侵略、好斗的名声在外,在西洋一带发动攻击、四处劫掠,很可能已经逼近清朝的陆上边界。因此,他们决定尽早打发他,让他越快离开中国越好。勋爵返回英国,除了转呈乾隆致英王的几封盛气凌人的回信,几乎一无所获。
虽然马戛尔尼表面若无其事,但他和使团成员都感到受了羞辱。欧洲的批评令他们如芒在背,他们于是越发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清廷,称清廷自大、顽固、对英国的厉害视而不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呼应;在后续的外交努力失败后,许多英国人开始认为,必须通过展示实力来反制中国的傲慢无礼。他们讲述关于中国如何冥顽不灵的故事,马戛尔尼使团成了必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不允许英国在国家间天然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外交,所以使用武力就是顺理成章的。
对中国的这种负面看法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公众和决策者,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促使他们将中西方交流的历史看作一场文化的冲突。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天下秩序”或者说“朝贡体系”与西方独立国家之间的外交制度是无法相容的。故事演进下去,结局就是冲突。因无法与中国在平等基础上互动而倍感受挫的欧洲人断言,必须把中国纳入西方国际体系,且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在他们眼中,西方国际体系才是国家间互动的自然模式。这样的相互关系导致中欧之间在19世纪爆发激烈的冲突: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等等。中西方学者都提出,清朝的僵化是19 世纪中国动乱杀戮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提法,并指出清朝统治者比人们此前以为的更务实,思维也更国际化;他们与西洋人的关系遵循现实政治;西方的外交也远非人们普遍形容的那样“现代”,那样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是深受欧洲以外外交实践的影响。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是这一时期与英国外交对比最鲜明的反例之一,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方关系的理解;然而,他们此行不只遭到忽视,更遭到了误解。多方资料显示,荷兰人毫无疑问受到了热情款待。大使德胜自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上司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明确指出德胜圆满地完成了指派的任务。使团确实没有宏伟的目标,也没有达成任何条约或协定:其主要目的就是来祝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年,从而加强荷兰与清朝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诡异的是,众多学者坚持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失败,而事实显然不是。
那么,荷兰使团为什么被抹黑了?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符合文化冲突的叙事模式。这种负面的描述始于为乔治·马戛尔尼总管贡物的吧龙(John Barrow)。吧龙在其畅销书《中国行记》(Travels in China)中,花费16页的篇幅攻击荷兰使团。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荷兰人在被要求叩头行礼时悉数照做,但顺从没有用处,他们还是被一心要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中国宫廷故意羞辱了。他认为,荷兰人的顺从实际上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低声下气,”他写道,“乖乖服从于这个自大的朝廷提出的有辱尊严之要求,只会令它更加自负,强化其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荒唐念头。”马戛尔尼或许未能实现他的目标,但至少他坚定的态度迫使中国人意识到英国人比他们优越——哪怕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吧龙对荷兰使团的解读被广泛接受,现代学者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比如,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部就曾提到:“英国与荷兰的使团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前者保存了尊严,后者颜面尽失。
荷兰人的“东方式外交”和商业成功
但荷兰大使很清楚他在清廷的角色,也理解东亚外交的理念和做法。德胜是研究日本的学者,曾两度率团前往江户,在幕府将军面前叩头。他明白东亚的外交不在于提要求或谈“生意”,更注重的是相互关系中的礼法规矩。
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胞并没有什么不同。荷兰人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东亚世界,并且通常都是按照这里的规矩行事。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成立不久,就直闯中国海,炮火齐发,要求贸易特权。当公司的领导者不能遂其所愿,便兵戎相向。明朝官兵反击,在中国海岸及周边的多场交战中力克该公司。得到教训的荷兰人懂得了恭顺,也得到了中国贸易的回报,中国货物流向了他们在亚洲的前哨。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荷兰人又派出了第一个被清廷接见的西方使团,荷兰使者没有反对叩头行礼。1700年之前,又有两个荷兰使团受到朝廷接见,每个使团都按照标准的礼节行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大发其财。
当公司在日本与强大的德川幕府相遇时,荷兰人也顺服了。公司起初曾在日本做出咄咄逼人的举动,之后同样被迫接受了扮演一个温顺的角色,每年派出使团,如同日本各地的藩主一样到幕府叩头。就像在中国一样,良好的行为得到了报偿。荷兰人是唯一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西方人,而日本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与此同时,荷兰人在其殖民地首府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也设立了自己的亚洲“朝廷”(吧城荷印当局)。他们接待来自亚洲各地乃至非洲的代表,采纳东南亚和东亚外交场上的仪注和做派,比如华盖和大象仪仗队。正如历史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所指出的:“巴达维亚政府在亚洲的统治者中间取得了一席之地,学会了遵守当时亚洲通行的外交礼仪和规则。荷兰殖民者也确实迫于需要发明了‘东方式’礼仪,从而符合既有的外交互动规则。”
就这样,荷兰人逐渐理解并基本上接受了包乐史所说的“东方式外交”(Oriental Diplomacy)。他们领悟到,东亚的国际关系由截然不同的典型思想支配着:关系有明确的尊卑之分;遣使多是为了庆贺而非谈判;互动交往通常以礼仪为依归,其中很多礼仪都以中国古代传统为基础。
荷兰不是唯一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非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的国家。新外交史学(New Diplomatic History)的研究者已经指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外交远比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更具临时性、更缺乏系统性,欧洲人经常参与多种类型的外交实践,甚至连英国人都掌握了基本的东亚外交礼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
这本书不只关于一个使团,还关于一段段相遇。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它描述了这些异国旅客与人的相遇,与中国的制度、习俗、技术和风景的相遇。但是,它也探索了观点的相遇:他们从欧洲万卷书中得来的看法与他们在中国万里路上所见现实之相遇。
“一个人不应该以本国的风俗习惯去评判他国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旅行者应当入乡随俗。”这倒不是说使团的翻译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热爱中国——他也很能挑刺儿——而是说他感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的行事标准与他们和客人打交道时是一样的。“对于待人同待己的人,我们又能指责什么呢?”一个人应该接受中国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把它当成心目中希望的样子。“我并不倾慕中国人,”他写道,“但我不偏不倚,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想法对他们评头论足。”小德经并非一向如他自称的这般公正,但这几句话很有道理。可惜的是,它们几乎都被人遗忘了,吧龙的观点却传播开来;对中国的消极看法和轻视态度在19世纪的英语世界内外几乎变得无处不在。
小德经的文字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影响力也不及英国人的记述,一个原因在于,荷兰共和国本身已不复存在。范罢览与乾隆皇帝一起喝茶的时候,法国军队正进入阿姆斯特丹。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的接替者巴达维亚共和国,是法兰西的傀儡国。这意味着,荷兰此时成了英国的交战国。英国占领了荷兰的船只和领地,导致在华荷兰人连购买日常必需品的经费都没有了。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办不下去了。与此同时,中国深受起义之扰,曾盛情款待荷兰使者的老皇帝将皇位传给儿子,而这位继任者在戡乱时显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中国恢复太平之际,和平也几乎同时重返欧洲。然而,这时世界已经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使团在华期间建立的前途无量的关系从此不再为世人所追求。
回到欧洲,几乎没有出版商对这种题材感兴趣:一个由已经消失的公司派出、代表已不存在的国家的外交使团。因此荷兰使团成员的作品,以及他们相对不具偏见的观点、对王朝官员友好交流的描述、在北京所受的接见、参加的筵宴、寺庙之行,以及参观内廷的经历,全部被遗忘了。相反,他们的使团被描绘成“文化冲突”的一部分: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外交优先权争夺之战,中国最终学会了谦逊,并被强行纳入了现代外交秩序。
(本文摘自《最后的使团》序言《文化冲突?》,大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发表时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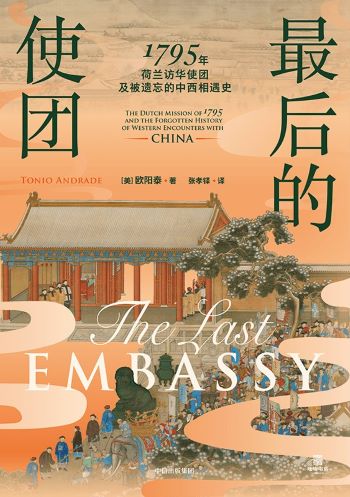
《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美]欧阳泰(Tonio Andrade)著 张孝铎 译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25年9月版
以下内容为友情赞助提供

全网新项目分享交流群
扫码进群,获取最新项目资讯
文档于: 2025-12-17 10:16 修改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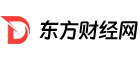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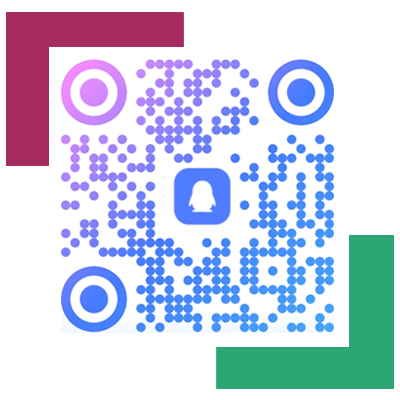






评论列表
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的荷兰使团,为何被历史遗忘?...
1794年,乾隆皇帝准备举行登基六十年庆典。臣子奏请大办新春盛典:摆筵席,放烟火,办诗会,唱大戏。王公大臣将来颂贺;价值连城的礼物将进献至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和最宏伟的园林;满洲贵...